译文及注释
译文
月亮被层云笼罩,阵阵晚风吹动悬挂在画檐下的铁马铜铃,叮当作响,这使得人更加感到悲凉凄切。起身挑挑灯芯,想把自己所有的思念、所有的悲苦、所有的怨恨都写下来说给心上人听,可是又长叹一声,想把灯吹灭,不再写了。
注释
双调:宫调名。寿阳曲:曲牌名,又名“落梅风”。
风弄铁:晚风吹动着挂在檐间的响铃。铁:即檐马,悬挂在檐前的铁片,风一吹互相撞击发声。
两般儿:指“云笼月”和“风弄铁。”凄切:十分伤感。
剔银灯:挑灯芯。银灯,即锡灯。因其色白而通称银灯。
吁气:叹气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,往往设身处地,曲尽其致。这首小令,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,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。
起首两句,写云层遮住月亮,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。前者为色,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;后者为声,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,所以接下去说“两般儿助人凄切”。用一个“助”字,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。这“两般儿”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,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。
思妇对这“两般儿”如此敏感,是因为她独守长夜。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,亟须排遣,于是就有了四、五两句的情节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,思妇将它剔亮——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。剔亮银灯的目的,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,好寄给远方的丈夫。却不料一声长叹,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。这两句针线细密:“剔银灯”回应“云笼月”,云蔽月暗,光线昏淡,加上银灯又不争气,灯焰将尽,故需要“剔”;而“长吁气”则暗接“风弄铁”,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,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,如今居然“一声吹灭”,足见长吁的强烈。这个小小的片段,既出人意外,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;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,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。这个结尾堪称出色。灯到底吹灭与否,作者未明言说破,或是故意不说破,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,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,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。可谓”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“(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引梅尧臣语)的诗理。
《彩笔情辞》载卢挚的《寿阳曲·夜忆》四首,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,全文是:“窗间月,檐外铁,这凄凉对谁分说。剔银灯欲将心事写,长吁气把灯吹灭。”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,不过末句是“一声吹灭”比“把灯吹灭”更有韵味。又《乐府群玉》有钟嗣成《清江引·情三首》,其一曰:“夜长怎生得睡着,万感着怀抱。伴人瘦影儿,唯有孤灯照。长吁气一声吹灭了。”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,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。
参考资料:
马致远(1250年-1321年),字千里,号东篱(一说字致远,晚号“东篱”),汉族,大都(今北京,有异议)人。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、白朴等人,生年当在至元(始于1264)之前,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(1321—1324)之间,与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,是我国元代时著名大戏剧家、散曲家。
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,谓之命;其赋于人,谓之性。其主于身,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「乐」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六经也,由之富家者支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,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为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: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」何以异于是?
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,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?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冈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,又为尊经阁于其后,曰:「经正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,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去去倦寻路程。江陵旧事,何曾再问杨琼。旧曲凄清。敛愁黛、与谁听。尊前故人如在,想念我、最关情。何须渭城。歌声未尽处,先泪零。
 马致远
马致远 李煜
李煜 王守仁
王守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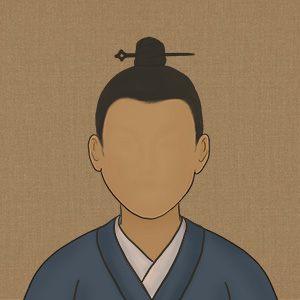 周文质
周文质 周邦彦
周邦彦 辛弃疾
辛弃疾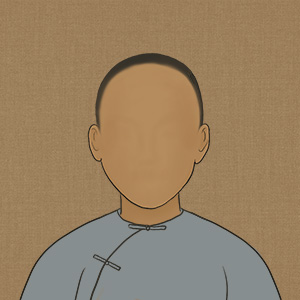 刘镇
刘镇 张抡
张抡 毛滂
毛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