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骊山峰峦横亘,渭河环流,两岸景色秀丽,曾经秦国地势险峻,如今险要的山川依旧。狐兔悲鸣伤慨,草木萧瑟凋零,劳民伤财的秦宫隋苑已成废墟,巍峨的唐宫汉陵而今又在何处?山,空自忧愁;河,空自奔流。
注释
中吕:宫调名,元曲常用宫调之一。
山坡羊:曲牌名,北曲属中吕宫,基本句式为十一句,四十三字。
骊山:在今陕西临潼东南,秦始皇陵在其下。
岫(xiù):峰峦。
秦宫:秦始皇的离宫,隋炀帝的东都(洛阳)西苑,徒然遗下臭名。
赏析
散曲名家张养浩用“山坡羊”写过九首怀古曲,以《潼关怀古》一首,最为著名;赵善庆的这首《长安怀古》可谓与之同曲而同工。
骊山在长安附近的临潼县东南,渭水环绕着长安。这一山一水,用“横”“环”二字,不仅点明所咏之地是长安,而且把这历代古都形势之险峻、景色之壮丽,全都烘托而出。此种手法与南宋词人姜夔《扬州慢》词起句“淮左名都,竹西佳处”,极为相似皆以重拙之笔开篇,而与后面的残破之景、黍离之悲形成强烈的反跌。“山河百二还如旧”,意谓秦国地处险要,二万人足以当诸侯百万人。如今长安形势,只有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。“还如旧”三字,顿挫有力,作者百感交集的怀古之情,尽在其中。后面的“狐兔悲,草木秋;秦宫隋苑徒遗臭,唐阙汉陵何所有”,一气而下,倾吐出作者由今思昔而产生的慨叹、感伤和悲往日秦汉隋唐紫华似锦的都城,今朝狐跑兔走,草木丛生,荒芜颓败,冷落凄凉。“狐兔悲,草木秋”是作者当时所见的景象,这同长安一带具山河之险的优越形势形成强烈的对照,山河依旧,而“秦宫隋苑”“唐阙汉陵”——历史上以长安为都的王朝和它们的君主如秦皇、汉武、隋文、唐宗,曾几何时赫赫扬扬,如今烟消云散什么也没了。正如苏东坡在《赤壁赋》中所云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“秦宫隋苑徒遗臭,唐阙汉陵何处有”,其中有作者吊古伤今,为历史人物慨叹的情绪;亦含有对历代统治者花费浩大的人力物力,兴建了豪奢的宫苑阙陵,但在改朝换代中往往化为灰烟而表现出的愤懑。作者写这两句时,秦隋并提,斥之为“徒遗臭”,遗责的成份较重,这大概是因为秦始皇、隋炀帝是著名的穷奢极侈的暴君,而秦、隋两朝又短哲早亡之故。对汉唐就要客气些,只说“何处有”。当然,在抒发今昔兴亡之感的同时,也来杂着作者人生无常、转瞬即逝,徒唤奈何的人生观。最后两句“山,空自愁;河,空自流”,作者从怀古的沉思中复又回到眼前的景中来,经过一番遐想,再看那“横岫”的山,似乎也在怀古而生恨发愁;“环秀”的渭水,好像也因怀古而汨汨叹息。这是移情入景的手法。然而,“古”只能供“怀”不能再回生,水也罢,山也罢,就如同人只能发怀古之幽思一样,也只能“空自愁”,“空自流”。
这首小令以山水起,又以山水结,起是写实景;结是景生情由景而情,前后呼应在结构上严谨而巧妙,格调上也深沉而苍凉。▲
创作背景
《山坡羊·长安怀古》为咏史怀古之作。作者时在长安,见骊山渭水山河依旧而秦宫隋苑唐阙汉陵已荒芜,因生怀古之叹,作此散曲。
赵善庆(?-1345年后),元代文学家。一作赵孟庆,字文贤,一作文宝,饶州乐平(今江西乐平县)人。《录鬼簿》说他「善卜术,任阴阳学正」。著杂剧《教女兵》、《村学堂》八种,均佚。散曲存小令二十九首。《太和正音谱》称其曲「如蓝田美玉」。
昆山徐健菴先生,筑楼于所居之后,凡七楹。间命工斫木为橱,贮书若干万卷,区为经史子集四种。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,史则日录、家乘、山经、野史之书附焉,子则附以卜筮、医药之书,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。凡为橱者七十有二,部居类汇,各以其次,素标缃帙,启钥灿然。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:“吾何以传女曹哉?吾徐先世,故以清白起家,吾耳目濡染旧矣。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,每欲传其土田货财,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;欲传其金玉珍玩、鼎彝尊斝之物,而又未必能世宝也;欲传其园池台榭、舞歌舆马之具,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。吾方以此为鉴。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?”因指书而欣然笑曰:“所传者惟是矣!”遂名其楼为“传是”,而问记于琬。琬衰病不及为,则先生屡书督之,最后复于先生曰:
甚矣,书之多厄也!由汉氏以来,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,其下名公贵卿,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,或亲操翰墨,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。然且裒聚未几,而辄至于散佚,以是知藏书之难也。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,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,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。是故藏而勿守,犹勿藏也;守而弗读,犹勿守也。夫既已读之矣,而或口与躬违,心与迹忤,采其华而忘其实,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,与弗读奚以异哉!
古之善读书者,始乎博,终乎约,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,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。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:沿流以溯源,无不探也;明体以适用,无不达也。尊所闻,行所知,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!
今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,上为天子之所器重,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,藉是以润色大业,对扬休命,有余矣,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,俾后先跻巍科,取宦仕,翕然有名于当世,琬然后喟焉太息,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!循是道也,虽传诸子孙世世,何不可之有?
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。居平质驽才下,患于有书而不能读。延及暮年,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,耳目固陋,旧学消亡,盖本不足以记斯楼。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,姑为一言复之,先生亦恕其老誖否耶?
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,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亟矣,今悉兵以临赵,赵必亡。赵,魏之障也。赵亡,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,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,赵、魏亡,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,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,亦以救魏;救一国者,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,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,夫奚不可者?
然则信陵果无罪乎?曰: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,信陵君之心也。
信陵一公子耳,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,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,是赵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,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,欲急救赵,是信陵知有婚姻,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,非为魏也,非为六国也,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,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,而在他国,则虽撤魏之障,撤六国之障,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,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,虽赵亡,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,不能当一平原公子,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,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,可也,不幸战不胜,为虏于秦,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,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夫窃符之计,盖出于侯生,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,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,是二人亦知有信陵,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,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,不听,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,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,不听,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,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,不听,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,王亦必悟矣。如此,则信陵君不负魏,亦不负赵;二人不负王,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?信陵知有婚姻之赵,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,外则邻国,贱则夷门野人,又皆知有公子,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呜呼!自世之衰,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,有重相而无威君,有私仇而无义愤,如秦人知有穰侯,不知有秦王,虞卿知有布衣之交,不知有赵王,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,信陵之罪,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,为六国也,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,为一亲戚也,纵求符于王,而公然得之,亦罪也。
虽然,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,信陵亦安得窃之?信陵不忌魏王,而径请之如姬,其素窥魏王之疏也;如姬不忌魏王,而敢于窃符,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,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?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?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?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?履霜之渐,岂一朝一夕也哉!由此言之,不特众人不知有王,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,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!圣人之为虑深矣!
年愿。
【雁儿落】常想西湖舣画船,北苑开春宴。一声金缕令,七换梁州遍。
【德胜令】今日小亭轩,羞到杏花边。黯黯愁成阵,厌厌日胜年。嫣然,一
笑春风面;无缘,灯前云髻偏。
【雁儿落】春衫和泪穿,犹认伊针线。玉箫深夜品,多是君愁怨。
【水仙子】别来几见月儿圆,每为嫦娥惜少年。画堂深隔断归来燕,玉钩闲
帘未卷,一天情着个谁传?想一饷心间事,写一幅肠断篇,等一个孤雁回旋。
【雁儿落】艳阳三月天,寿酒筵前劝。可怜张解元,不赴蟠桃宴。
【挂玉钩】爱杀槎头缩项鳊,皆上金盘荐;笑杀池中并蒂莲,未许东风见。
援紫毫,磨端砚。屈曲银钩,细草鸾笺。
【尾】沉沉烟锁垂杨院,迟迟月上桃花扇。罗帕新词,聊寄情缘。唱道张京
兆心专,周琼姬苦意坚。怕几阵东风吹落残花片,恁时绿暗红嫣,兀谁管春山翠
眉浅。
 赵善庆
赵善庆 汪琬
汪琬 唐顺之
唐顺之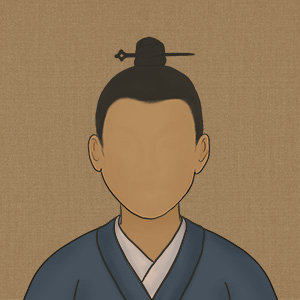 刘庭信
刘庭信 李致远
李致远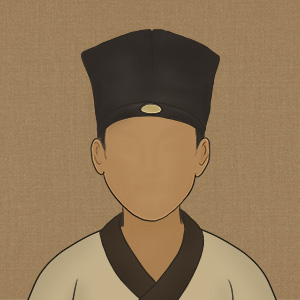 施绍莘
施绍莘 乔吉
乔吉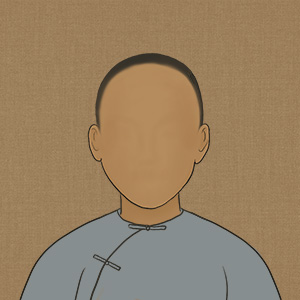 王质
王质 张抡
张抡 石孝友
石孝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