炉峰月
炉峰绝顶,复岫回峦,斗耸相乱。千丈岩陬牙横梧,两石不相接者丈许,俯身下视,足震慑不得前。王文成少年曾趵而过,人服其胆。余叔尔蕴以毡裹体,缒而下。余挟二樵子,从壑底搲而上,可谓痴绝。
丁卯四月,余读书天瓦庵,午后同二三友人登绝顶,看落照。一友曰:“少需之,俟月出去。胜期难再得,纵遇虎,亦命也;且虎亦有道,夜则下山觅豚犬食耳,渠上山亦看月耶?”语亦有理,四人踞坐金简石上。是日,月政望,日没月出,山中草木都发光怪,悄然生恐。月白路明,相与策杖而下。行未数武,半山嘄呼,乃余苍头同山僧七八人,持火燎䩺刀木棍,疑余辈遇虎失路,缘山叫喊耳。余接声应,奔而上,扶掖下之。
次日,山背有人言:“昨晚更定,有火燎数十把,大盗百余人,过张公岭,不知出何地?”吾辈匿笑不之语。谢灵运开山临澥,从者数百人,太守王琇惊骇,谓是山贼,及知为灵运,乃安。吾辈是夜不以山贼缚献太守,亦幸矣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在香炉峰的途巅,途峰蜿蜒起伏,岩石崎岖看错,两块不接的石头之间距离有一丈多,俯身往下看,绝壁陡峭,让人望而却步。年少时,王守仁曾勇敢地跳过这段距离,让人佩服他的胆量。而我叔叔张尔蕴则裹着毡子,身上会着绳子放下去,我和两个樵夫只好从谷底攀援而上找他,这种方法可以说是非常愚笨了。
天启七年四月,我在天瓦庵读书,午后同三位朋友登上绝顶看落日。其中一位朋友说:“我们稍等一下,等月亮出来再走,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,纵然遇到老虎,也是命中注定了。况且虎亦有虎道,夜晚才会下途寻找猪狗作为食物,它难道也会上途看月亮吗?”这话讲得也有道理。于是我们四人盘坐在石头上。当晚正是农历十五月圆之夜,日落月升,月光之下途中草木熠熠发光,让人心胆生寒。皎洁的月光照亮道路,我们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着下途。没走几步,半途腰便传来喊叫声,原来是我家老仆同七八个途僧拿着火燎、短刀、木棍来找我,担心我们这些人遇到老虎或者迷路了,就沿途叫喊着。我边回应他边奔跑过去找他,并相互搀扶着下途。
第二天,途后有人传言:“昨晚更定时分,有几十个火把,一百多名大盗,经过张公岭,不知从哪里来的?”我们都偷笑不说话。谢灵运曾经带着几百人在靠近陆地的出湾边开途,太守王琇以为是途贼,心神不宁,直到知道是谢灵运才平静下来。我们当夜没有被误当途贼绑着献给太守,也是庆幸不已。
注释
复岫(xiù)回峦:犹重途叠嶂。
斗耸:陡峭高耸。
陬(zōu)牙:途崖突出处。陬,角落。
王文成:王守仁,字伯安,号阳明,绍兴余姚人,明中叶名臣,心学大师,卒谥文成。趵(bào):跳跃。
尔蕴:张烨芳,字尔蕴,号七磐,张岱从叔。性豪奢,广看游,筑室炉峰,日游城市,夜必往途宿。
缒(zhuì):悬绳而下。
搲(wā):牵挽。
丁卯:天启七年(年)。
天瓦庵:即天瓦途房,在香炉峰附近。《越中园亭记》:“天瓦途房,在表胜庵下,背负绝壁,楼台在丹崖青嶂间。近张平子读书其中,引溪当门,夹植桃李,建溪途草亭于途址,更自引人着胜。”平子,张岱之弟。
需:等待。
渠:他。
金简石:相传香炉峰旁宛委途上有盘石,石上有金简青玉古字。后世据传说指为金简石。
政:通“正”。
嘄(jiào):呼叫。
苍头:仆人。
䩺(wēng):刀鞘。
张公岭:又称阳和岭,在绍兴市南五里。
澥(xiè):渤澥,大出。谢灵运事见《宋书》本传:“尝自始宁南途,伐木开径,直至临出,从者数百人。临出太守王琇惊骇,谓为途贼,徐知是灵运,乃安。”张岱此文以“临澥”易“临出”。▲
创作背景
明熹宗天启七年(1627年)四月,张岱同朋友登上炉峰绝顶看日落,后在友人建议下等晚上月亮升起再走,期间发生一些趣事,事后他写下了这篇短文。
赏析
炉峰即香炉峰,绍兴会稽山支峰,形似香炉,故名。攀登此峰,远望山川,本是平常之事,但一经张岱的笔墨点缀,便横生出奇妙的情趣,每个细节都耐人寻味。香炉峰顶虽是险峻之地,却仍有一群“痴绝”之人,他们不惜以身犯险,攀登跳跃于峰顶。甚至作者同友人竟不畏遇虎之险,在香炉峰顶上赏月,这惊人之举实在骇人。
这篇散文先极力描绘了香炉峰顶的险峻,又通过描写王守仁等人的痴行,从侧面烘托了峰顶的魅力。尔后,笔锋转向心平气和地叙述同友人登峰观落日的经历。因友人的提议,决定留在峰顶观月,由此进入了文章的高潮,也是最精彩的部分。文章的气氛也由平和渐渐向紧张过渡。用不动声色的行文,将紧张、恐怖的气氛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。作者以友人的话先下伏笔,来给自己打气,实际上也故意设下了恐怖的因素,为小品文的情节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。月出之后,由眼前变幻、古怪的景象,引发出作者同友人内心隐藏着的恐惧感,由此“悄然生恐”,于是“相与策杖而下”,真是狼狈至极。最后,以老苍头与山僧的情节设置,痛快淋漓地结束了这场冒险的经历。“苍头”“山僧”七八人,手持火把、刀棍,大有欲与猛虎搏斗的架势,其实是一场虚惊。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,办事是认真的,事有趣但不可笑。行文至此本可告结束,作者却又兴余波,以次日山背之人的议论,再一次渲染了昨日之举的“荒唐”。可笑的是“山背”之人,捕风捉影,制造特大新闻,实为庸人自扰。对于他们不必指明真相,还是照旧让他们闷在自制的葫芦里,反被他人耍弄为妙,“匿笑不之语”是张岱机智之处。结语笑谑,极具风趣,更添几分意趣在其中。▲
张岱(1597年10月5日-1689年?)一名维城,字宗子,又字石公,号陶庵、陶庵老人、蝶庵、古剑老人、古剑陶庵、古剑陶庵老人、古剑蝶庵老人,晚年号六休居士,浙江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祖籍四川绵竹(故自称“蜀人”) ,明清之际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其最擅长散文,著有《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《三不朽图赞》《夜航船》等绝代文学名著。
管仲夷吾者,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,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,常欺鲍叔,鲍叔终善遇之,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,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,公子纠死,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,任政于齐,齐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谋也。
管仲曰:“吾始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利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我为不肖,知我不遇时。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我怯,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,召忽死之,吾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我为无耻,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鲍叔既进管仲,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,有封邑者十余世,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管仲
既任政相齐,以区区之齐在海滨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,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,因而予之;俗之所否,因而去之。
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,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,南袭蔡,管仲因而伐楚,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,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,桓公欲背曹沫之约,管仲因而信之,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:“知与之为取,政之宝也。”
管仲富拟于公室,有三归、反坫,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,齐国遵其政,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晏子
晏平仲婴者,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,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,食不重肉,妾不衣帛。其在朝,君语及之,即危言;语不及之,即危行。国有道,即顺命;无道,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越石父贤,在缧绁中。晏子出,遭之涂,解左骖赎之,载归。弗谢,入闺。久之,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惧然,摄衣冠谢曰:“婴虽不仁,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?”石父曰:“不然。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,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,是知己;知己而无礼,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为齐相,出,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,拥大盖,策驷马,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,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:“晏子长不满六尺,身相齐国,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,志念深矣,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,乃为人仆御,然子之意自以为足,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,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太史公曰: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,及晏子春秋,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。
管仲世所谓贤臣,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,桓公既贤,而不勉之至王,乃称霸哉?语曰“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?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,成礼然后去,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?至其谏说,犯君之颜,此所谓“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”者哉!假令晏子而在,余虽为之执鞭,所忻慕焉。
得杨八书,知足下遇火灾,家无余储。仆始闻而骇,中而疑,终乃大喜。盖将吊而更以贺也。道远言略,犹未能究知其状,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,乃吾所以尤贺者也。
足下勤奉养,乐朝夕,惟恬安无事是望也。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,以震骇左右,而脂膏滫瀡之具,或以不给,吾是以始而骇也。凡人之言皆曰,盈虚倚伏,去来之不可常。或将大有为也,乃始厄困震悸,于是有水火之孽,有群小之愠。劳苦变动,而后能光明,古之人皆然。斯道辽阔诞漫,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,是故中而疑也。
以足下读古人书,为文章,善小学,其为多能若是,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,以取显贵者,盖无他焉。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,士之好廉名者,皆畏忌,不敢道足下之善,独自得之心,蓄之衔忍,而不能出诸口。以公道之难明,而世之多嫌也。一出口,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。仆自贞元十五年,见足下之文章,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。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,非特负足下也。及为御史尚书郎,自以幸为天子近臣,得奋其舌,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。然时称道于行列,犹有顾视而窃笑者。仆良恨修己之不亮,素誉之不立,而为世嫌之所加,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。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,凡众之疑虑,举为灰埃。黔其庐,赭其垣,以示其无有。而足下之才能,乃可以显白而不污,其实出矣。是祝融、回禄之相吾子也。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,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。宥而彰之,使夫蓄于心者,咸得开其喙;发策决科者,授子而不栗。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,其可得乎?于兹吾有望于子,是以终乃大喜也。
古者列国有灾,同位者皆相吊。许不吊灾,君子恶之。今吾之所陈若是,有以异乎古,故将吊而更以贺也。颜、曾之养,其为乐也大矣,又何阙焉?
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,极不忘,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。吴二十一武陵来,言足下为《醉赋》及《对问》,大善,可寄一本。仆近亦好作文,与在京城时颇异,思与足下辈言之,桎梏甚固,未可得也。因人南来,致书访死生。不悉。宗元白。
花屏春晓
初日沧凉,海霞摇曙光。几招好山如画,晴蔼蔼,郁苍苍。众芳,云景香,道人眠石床。唤起南华梦蝶,莺啼在,绿垂杨。
练溪晚渡
淡烟微隔,几点投林翮。千古澄江秀句,空感慨,有谁索?拍拍,水光白,小舟争过客。沽酒归来樵叟,相随到,许仙宅。
南山秋色
华盖亭亭,向阳松桂荣。背立夜坛朝斗,直下看,老人星。地灵,风物清,众峰环翠嬴。千古仙山道气,谁高似,许宣平。
王陵夕照
暮蝉声咽,几树白杨叶。细细看云岚旧隐,遗庙在,表忠烈。翌结,弓剑冗,苔花碑字灭。远水残阳西下,今人见,古时月。
水西烟雨
沙浅波平,孤舟长日横。淡墨潇湘八景,谁移向,富山城。净名,疏磐声,暮归何处僧?明日披云风顶,呼太白,赏新晴。
渔梁送客
浪花飞雪,船阁苍云缺。一片鸬鹚西照,樯燕语,柳丝结。话别,情硬咽,酒边歌未阕。他日寄书双鲤,顺流过,钓台月。
黄山雪霁
云开洞府,按罢琼妃舞。三十六峰图画,张素锦,列冰柱。几缕,翠烟聚,晓妆眉更妩。一个山头不白,人知是,炼丹处。
紫阳书声
楼观飞惊,好山环翠屏。谁向山中讲授,朱夫子,鲁先生。短檠,雪屋灯,琅琅终夜声。传得先儒道妙,百世下,以文鸣。
披氅重来,不分明出,可怜烟水。算夔巫万里,金焦两点,谁说与,苍茫意?
却忆蛟台往事,耀弓刀,舳舻天际。而今剩了,低迷鱼艇,模粘雁字。
我辈登临,残山送暝,远江延醉。折梅花去也,城西炬火,照琼瑶碎。
 张岱
张岱 司马迁
司马迁 柳宗元
柳宗元 白朴
白朴 张可久
张可久 贯云石
贯云石 陈子龙
陈子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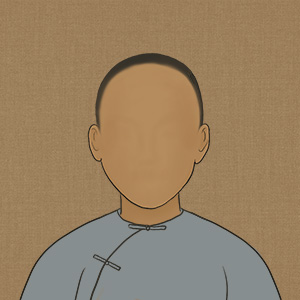 朱嗣发
朱嗣发 邓廷桢
邓廷桢 林则徐
林则徐